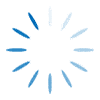他顿了顿,又道:“记住,是急事!小毛病别来烦我。”
我失笑:“好,我记得了。”
他颔首,动作干脆利落,收拾好药箱,站起身准备离去。
可走到门前时,他忽然顿住,回头望了我一眼,留下一句极有深意的话。
“有些事得抓紧。眼疾尚可医,虽遗憾,也还能救。”
他顿了顿,像是故意让那句子在空中凝了一瞬,才慢慢道:“但人若没命了,可就真是——回天乏术了。”
说完,他走得洒脱,留我一人呆愣在原地,心重重沉了下去。
第二日一早,兆神医连招呼都没打就离开了。
也正因这份利落得近乎冷漠的告别,反倒令我心底那股不安愈发沉重。
尤其是他临行前的那句话。
那语气太平淡,像一句随口而出的闲谈,却偏偏让人越想越心慌。
我控制不住地开始胡思乱想。
尤其是那一直安放在我枕边的玉佩,竟无声地裂出一道细纹,仿佛一种不好的征兆。
李昀……难道真的出了什么事?
这念头一冒出来,胸口便一点一点地收紧。
懊悔随之而来。
我当时就不该那样在家安坐,应该去看他一眼的。哪怕只遣人去探,也好过现在这般一无所知。
所有最坏的念头在脑海中一一袭来,越想越觉得真切,好像已然发生了一般。
那种类似宿命般,再也无缘得见的感觉越来越强烈,强烈到让我恐惧。
——若此生再见不到他了呢?
这份恐惧一点点攀附上心头,像钩子一样,在血肉里来回牵扯。
直到京中管事回府交账,我终于有了可询问的人,便立刻将他叫来。
我问他:“这段时间,京中可有什么异动?……尤其是国公府那边。”
管事想了想,道:“大事倒没听说。不过前阵子,国公府好像有人病了。不知是老国公,还是世子爷,几乎日日请大夫入府。听说那些大夫出来时,都摇头叹气,面露难色。”
他的话还没说完,我只觉浑身的血气在一瞬间退了个干净,脑子乱成一团,耳边嗡嗡一片。
这一夜,我几乎未曾合眼,辗转反侧。
天一亮,还未来得及想清自己到底是为何如此,身体就率先做出了决定。
直接动身去京兆府。
我告诉自己,这并非一时冲动。
李昀为我冒险采药,至今也许仍带病在身。如今我眼疾将愈,亲赴登门致谢,也是理所应当。
我接着命人亲自去寻兆神医,一定要将他安全护送到京兆府,求他替李昀诊治。
如此,我才算是不亏欠李昀什么。
我曾说过,我与他早已两清。
可如今,他又为我做了这许多。若我依旧不闻不问,反倒成了我亏他。
只是……我心里明白。
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,说到底,不过都是借口罢了,只是为了掩盖我心口那股挥之不去的不安和害怕。
一旦下定决心,我走得很快。
起初尚还能自持,虽是加紧脚程,但并未彻夜兼程,心中仍存几分理智。
可直到途中换乘陆路,在一处酒馆歇脚时,忽听人低语,说国公府正在操办丧事。
我顷刻间僵在原地。
那一瞬,仿佛有只手从我胸膛中穿透而出,生生攫住心脏,连带着呼吸都一并剥夺。
脑海里,全是李昀满身鲜血的样子。
他那条垂落在地、毫无力气的右手,那张苍白至极的脸。
我不敢细想,也不敢开口去问一句,甚至连打听消息的勇气都没有。
我死死咬住下唇,只能一遍遍告诉自己:这未必是真的。只是谣言。也许是误传。
只要我不去求证,不亲口听见、不亲眼看到,它就不能成真。
那之后,我几乎是发疯了一般地往前赶路。
只想快一点,再快一点。
身边人见我神色愈发憔悴,眼底血丝遍布,也没人敢劝,只默默随行。
体力早已透支,可我不敢停。
因为一旦慢下来,哪怕只歇息一瞬,心口那股疯长的恐惧便会像藤蔓一般攀上来,将我整个人缠紧。
那种无法言说的焦灼与预感,仿佛来自命运的某种提示。
可随着离京兆府愈近,那不敢求证的真相,也如风般无孔不入,一点点灌入耳中。
我再没办法自欺欺人。
眼看城门在望,我终于支撑不住,身形一晃,昏然倒地。
连日积压的惊惧与疲惫,终在此刻如决堤般爆发。
高烧昏迷,整个人仿佛被丢入烈焰与寒水中交替炙烤,翻腾不休。
头重脚轻,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,更遑论继续赶路。
一闭上眼,梦魇便扑面而来,李昀的身影在混乱的梦境中层层叠叠。
一时,他高坐马背,目光如刃,神情冷峻。
一时,他低眉垂眸,眼底藏着隐忍柔情。
一时,又是他浑身是血。
画面重叠交错,如碎镜嵌入心头,一片一片割裂撕扯,痛得我几欲窒息。
恍惚中,有泪从眼角溢出,静静地,一点点濡湿了枕边。
待我醒来时,发现自己的手放在心口处,掌中紧紧攥着那枚带着裂痕的玉佩,指节泛白。
风驰推门而入,见我睁开眼,神色一紧:“爷,您可算醒了。”
“我睡了几日?”我嗓音嘶哑,满口是药的苦涩,还透着浓浓的病气。
“三日。”风驰答道。
竟然睡了这么久。
我猛地闭了闭眼睛,心脉像受损一般,心口一动,眼前又是一片漆黑。
“爷别急!”风驰赶忙上前,“兆神医说了,您万不能再情绪激动,小心伤着眼睛——”
我只觉喉间发苦,苦得像吞下胆汁。
我撑着床缘想起身,眼前一阵眩晕,细密的光点在眼底炸开。眼球似正在充血,刺痛发胀。
可我却毫不在意,只想着不能再耽搁了。
明明在能得知治好眼睛时,我是那么狂喜,整个人都陷入到一种对未来无限遐想的期待中。
在右眼能微微看到光亮时,我甚至不敢高声说话,唯恐这是一场梦,稍微大一点的声响好似都能将这美梦戳破。
可是,若这梦需要用一个人的命换来。我宁愿,永远活在黑暗里。
那股悔意让我无法呼吸,心如刀割。
我强撑着坐起,风驰的劝阻声一波又一波,雷霄等人也跟着进来,劝我再歇一日。
“我等不了。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,沙哑得几乎破碎,“我怕国公府无人照料……怕连个像样的葬礼都没有。”
风驰红着眼,声音发抖:“也许……也许是老公爷。我们派出去的人今晚就能回来,爷再等等吧。”
“不。”我打断他,嗓音仿佛浸满血,“我已经离他这么近了。”
无论他是……在,还是不在,我都要亲眼见一见。
只有亲自看到,才能安心。
第78章 倦鸟归巢
到了京兆府时,已是深夜。
夜深人静,月色藏在卷起的乌云之后,天地寂然无声。
我等不及,也未让随行之人跟着,独自一人到了国公府前。
府门虚掩,外头黑沉沉一片,连个守夜的人影都不见。
我站在门前,指尖微凉,深吸一口气,抬步走了进去。
府中一片沉寂,唯有一点灯火遥遥引路。
我循着那微光,穿过静默的廊道。
每一步都像踏在空处,声音被吞没,只余衣角拂动的细响。
灵堂就设在正厅,昏黄灯火晃荡不定,幽冷如水,森冷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我缓缓踏入堂中,只见一方漆黑的牌位立在案上,香烟缭绕,烛火跳动。
我怔在原地,还未看清灵牌上的字,双膝便突然一软。
好似被剥骨抽筋般,一下就跪坐在了地上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