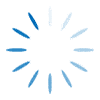金凤来信,将那日宴会的对话一字一句告诉他。银瓶奇道:“姐,父亲在外辛苦,咱们打听他的私事是不是不大好?”金凤心想,你真是记吃不记打,他辛苦什么,辛苦和水灵灵的小姑娘谈情说爱吗?
尉迟莲接到信,猜到皇帝有意放风敲打他。进了京城,萧湘多日留在宫内,不是值班就是赴宴。他找到郡主,她挤眉弄眼道:“殿下拿五百两当彩头,看谁能让萧湘中意。宫里人都偷偷下注。叔叔要是去,我压你赢。唉,晚来半天,我可就押宝青琅了。”
尉迟莲啼笑皆非,去了花园,丝竹管弦,伶人低吟浅唱,问:“大人,这是您家乡的小调,不知合不合您的意?”
“好好好。”她连连敷衍。
弹琵琶的美貌少年大胆开口:“大人一直走神,脸上一次也没笑过。”
“我生性木讷,在心里笑。”她打起精神应付。
少年咯咯笑了:“我不信,除非大人让我听到您心里的笑声。”萧湘耳朵嗡嗡的,好像听到黄莺叫个不停,一个字都听不进去。
“天气凉了,别在外头久坐。”尉迟莲坐下来,拉过她的手捂热,说,“又忘了喝药,手凉得很。”她转头,啜饮热茶,不说话。宫人认得尉迟莲,连忙屏退伶人。他们惹不起尉迟莲,又看萧湘待他不一样,不敢争锋,只能退避三舍。
皇帝走近,郡主迎上去,摇头摆手,皇帝望见两人拉拉扯扯,萧湘不似之前沉闷,虽是极力回避,却露出几分委屈神色来。笑着哼了一声,转身离开。郡主频频偷看,却见萧湘扭着脸不看人,心想,人说叔叔是熟透的藕——心眼儿多,我要瞧瞧他怎么起死回生。她放慢步子,再一看去,尉迟莲凑近亲吻她的脸颊。文君连忙咋舌耸肩快步跟上皇帝,他敢做,她还真不敢偷师咧。
萧湘被他弄得心里乱糟糟的,酸甜苦辣咸,混在一处,像落网的雀鸟,急不可待要一头撞出去,一狠心,铆足了劲,抓住他的手掰开,说:“算了!”他应声松开,耳边响起起身的响动,她放松了紧绷的筋骨,压下心头泛起的空落落。岂料尉迟莲转到她跟前,双臂紧紧箍住她,直直吻她的嘴唇。不像平时那样用力,轻轻软软密密的亲吻。他的气息随着涓涓的暖流从双唇蔓延到舌尖,然后是喉头。和酒水辛辣的滋味不一样,是绵密柔和,又无孔不入的。
萧湘像是被灌了迷药,浑身瘫软,手指都软绵绵的,她后悔招惹他。自己的伪装在他面前不堪一击,他轻而易举勾出她深藏的软弱姿态,不费吹灰之力击穿她的防线。她厌恶恐惧被人识破和控制的感觉,这很危险。她不能再一次犯下这样致命的错误。
他察觉轻微柔软的颤抖,隔着衣衫,摸到了微微潮湿的触感。轻轻缓缓,让她靠在肩上,柔声说:“好好休息,你太累了。”她的身躯像春水一样温软,眼波却像秋水柔软冰凉。她在调动记忆深处的极致的痛楚换取一丝冷静,撕裂旧伤,用自己的血来暖自己,不觉支离破碎。
他挪她进房间,炉火香暖,消弭秋寒,汗水也渐渐温热。尉迟莲解开她的衣衫,擦拭浑身汗水,安慰她:“别怕,没事了。”他细细碎碎哄她,将湿透的内衣和外衫都换了。萧湘脸色还是和病西施一样,但稍稍有了些精神。他叹道:“你太实心眼了。消遣也要费神,倦了只管和陛下说,回家歇息去。”
他的额头抵着她的,汗湿的碎发粘在他的肌肤上,她的肌肤温凉,些微的暖意若有若无。他的指尖触摸她下巴微微凸起的那粒痣,啄着眼角和面颊。他嫌盖被子不保暖,摩挲她的肢体,两人肌肤相亲,心中一荡,不觉情动,萧湘睁眼道:“你非礼我?”他亲了亲她的唇角,低笑软媚耳语:“好些天没见着了,你说怎么办。”她低头弄衣带,含含糊糊说:“那就那个吧,那个那个。”
她往他底下探,抓住他抬头的欲望,尉迟莲以为她用手纾解,直到她张了张口,低下头去,问:“你真要?”她迟疑说:“我也不能换个小的。”他被她一点一点吃下去,又扶着又含着,湿漉漉滑溜溜包裹。她跪着,一览无遗罗衫下柔滑的躯体。他稍稍一送,她就顶得不太舒服,他的膝盖夹住她的半身,手扶住她的头,调整她的吞吐节奏。
等结束了,他拔出来,让她吐掉,拿了帕子去擦她的嘴角。她的腿沾染余下的液,腿心晕开濡湿潮热。她问:“你还要?”尉迟莲耳鬓厮磨道:“这回不用进去。”他从背后搂着她,嵌在柔腻的腿间,脸埋进她汗津津的颈窝。两人交颈而眠,天色渐渐黑了,烛火微亮。他扶她起来穿衣吃饭。
尉迟莲问道:“你想住在宫里还是回家?”她说:“想去庙里,那里清静。”他说:“那也未必,青琅住着也六根不净。”她戳着瓜皮,说:“可以下山嫖。”他隔着罗裙轻轻一捏她的大腿,窃窃私语:“我知道你嫌宫里不自在,回家无聊,你来和我住上一段日子,凡事不用操心。”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