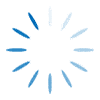可这样的雀跃没能持续多久,不知从哪起的气劲将之冲散成了雪碎。
小殷长澜呆立良久,哭得无声无息。
他却未能料到,随后能有意外之喜。
那个只是路过却不小心做了“坏事”的小影卫折返而回,三两下用剑削出个小雪人,放于他的掌心。
明明很冰,却仿佛让他感受到了灼烫的温度,惊喜万分。
可小雪人很快就融化了,当他完成课业再回来看时,只剩下一滩雪水,让他始终心心念念。
雪人不仅仅是雪人,影卫不仅仅是影卫。
是不期而遇的温度,是他的向往而未得。
然至今,有什么已然不一样了。
他立于最高位,先入目的,是万民的雪。
他要冰霜消融,万物复苏。
第45章 为臣(45)
罪帝已被处决的消息在不日后传出, 满朝欢庆。
与此同时,无数臣民奏请霁王继位,镇抚乱局。
摧信知道, 这即是对方的答复了。
殷长澜终是退了一步,给了他们一条生路。
也许这只是暂时性的, 毕竟他目前立足未稳,面临的挑战与事情太多,日后或有可能反悔。
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
离开的那一日, 城门外的风吹得很急,锟锏等人不约而同地前来相送, 亦是代表了其余那些常隐于暗处的影卫们的心意。
先前,他们被擒获而未被处死,这与宵练的求情不无关系。
对其结果亦有唏嘘,但锟锏心里明白,摧信之所以下狠手废了宵练,又何尝不是在给他们铺路?
要想活命,今后就只能于殷长澜麾下效力。宵练若在, 他们便很难得到重用,价值越大,才会越安全。
到了这样的关头, 他们就算有心,亦是说不出多好听的话来, 只会默默行动。
锟锏第一个上前。
他递过去的是块被磨得极薄的护心镜,边缘打了细密的孔,能穿绳系在衣襟里,很是精巧实用。
再是折钺,他笑嘻嘻地往摧信怀里塞了一本风月册子。
摧信不过是瞥了一眼封面, 脸色登时有了些许变化,但到底是师弟的心意,他还是没直接扔掉。
接着是独鹿,他手里拿着个小陶罐,罐口用红布扎得紧实,说:“去年秋里腌的肉干,用松烟熏过,搁半年也坏不了。路上烧锅热水,泡软了就能吃,顶饿。”
摧信将之接过时,罐身还留着些许温度,晃一晃,还能听见肉干碰撞的响。
最后是纯钧,送出的是两枚平安符。
他神情有些局促,似是觉得这并不够,随后再拿出一个样式简单却分量颇重的行囊。
其实那是摧信这些年攒下的银钱,他帮他从影门内室整理好带出来了,连带先前摧信借给其他影卫的那些,也都给一并讨回了。
摧信微顿,将收到的东西都放好,很郑重地看着他们。
道谢与告别都卡在喉头,他最终说出口的,唯一句“珍重”。
此别无期,愿你们日后。
剑锋所指,皆能得偿。
险局之中,自有退路。
摧信话音刚落,众人便听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传来。
循声望去,只见马背上的人玄袍猎猎,墨发亦被风掀起,正是殷无烬。他的袍角还沾着些尘土,却丝毫掩不住周身的洒脱恣意。
马蹄在离众人几步远的地方猛地停住,黑马前蹄立起,又很快稳稳落下。
殷无烬的目光扫过锟锏几人时,微微顿了顿。
四下忽然就静了。
锟锏几人的神情都略有些僵硬。
他们曾是殷无烬麾下锋刃,影卫的烙印里,刻着的第一重效忠便是他,如今却要改换门庭,这份尴尬就像根细刺,说不得,也咽不下。
殷无烬自是能看出其心中所想,却像是没察觉到这份凝滞。
他目光掠过他们,最终落在摧信身上,唇角勾起一抹笑,冲淡了眉宇间的冷意。
他伸出手,掌心朝上,姿态自然得仿佛只是寻常邀约,“走了。”
摧信没多言,握住了他的手,再顺势翻身上马,坐在殷无烬身后。
黑马似乎通人性,轻轻打了个响鼻,不安分地刨了刨蹄子。
直到这时,殷无烬才终于侧过脸,望向立在原地的影卫们。他没提过往,也没问将来,只扬了扬眉,声音里带着点戏谑却又坦荡:“无碍。”
黑马长嘶一声,旋即疾驰而去。
风卷着他的话音,清晰地落在每个人耳中。
“将你们影首赔于我就是。”
锟锏几人都是一怔,随即像是被这句话松了绑,紧绷的肩背微微松弛下来。
折钺率先笑了一声,又忍不住冲他们的身影扬声喊道:“我们影首轻功了得,可得看好别让他跑了!”
殷无烬没回头,笑声散在风里。
待马蹄声远了,影卫们仍未立即离开。
那些复杂的暖意,仿佛也融于心,尽数淌往彼此的前路去了。
*
前往边疆的路途实在遥远。
可战不容缓,他们必须尽快到达,便不能游山玩水。风尘仆仆,殷无烬就只剩下逗弄摧信这一大乐趣。
要说影首什么都好。
人帅能打,硬实力更是强到没边。
唯有一点就是,表达过心意后的影首变得更容易害羞,虽然看他的神情基本上是看不出来。
做事照旧强势,很有实干派的作风,却难抵言语上的撩拨。
而他一直都是只会否认,不肯承认。
殷无烬:“可曾厌?”
摧信:“无。”
殷无烬:“可会嫌?”
摧信:“不会。”
殷无烬:“可有爱?”
摧信默默地看他一眼,竟是直接红了耳尖。
殷无烬:“......”
其实答案已经很是明了,可他就是想多做确认,感受得更深刻几分。影首不会说甜言蜜语,但殷无烬想听,哪怕只是其表达出的只言片语。
闲着也是闲着,他还就非要逼得摧信破功不可。
过经一处佛地时,殷无烬出去了一趟,回来时手中拿着一支祈福竹签,据说是开过光的,极为灵验。
他向来是不敬神佛的,可这回,他恭恭敬敬地上阶请香,守足了规矩,才堪堪领到这一支。
殷无烬是给摧信带的,为其长姐而祈。
哪怕明知她被官兵抓走后凶多吉少,可又怎么会不存有一丝希冀?
他知他深藏的记挂与奢念。
摧信定定地看了他好一阵,这才极为专注地在签上落笔。
殷无烬只看了眼最下边的名字——尉荷衣。
原本姓尉。
他说:“长姐的名字真好听。”
摧信点点头。
于是他又说:“那你觉得,是叫殷无烬好听还是尉无烬好听?”
声音压得很低,透出若有若无的缱绻。
他现在是早已“身死”的罪帝,断不能再以原本的身份名讳出现在人前,恰好要冠个合适的姓氏。
还有什么能比“尉”更加合适?
而摧信的回应是,手中的笔“啪”一下落了地。
此后,摧信常常戴上面具。
殷无烬不可避免地被气到了。
以前摧信都是在出任务时才会戴面具,在他面前并不如此。
现在却偏偏相反,因为什么不言而喻。
生气归生气,置气却是不可能的。
当再次看到摧信在河边一丝不苟地给他洗衣服时,他还是不受控制地倾身靠近。
殷无烬想,自己色迷心窍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毕竟这样一位杀伐果断的影首,却给了他细致万般的柔情。
摧信的动作被迫中断,接受起来自心上人的热情。
殷无烬搂着他,慢慢将他面具下隐藏的绳扣含咬了个遍,手逐渐滑向他的衣服下摆,随即,似是不经意地笑了一声说:“影首大人,你在上面戴个面具能管什么用?”
摧信身体骤僵,下一刻竟是直接落荒而逃。
速度极快,霎时只留林叶摇晃和水流潺潺之声。
折钺居然一语成谶。
殷无烬再次不可避免地被气到了。
而另一边,摧信离至五里外才堪堪停下。
映入眼帘的是另一片景象。
漫山桃花灼灼,粉白绯红铺了半坡。风过时花枝轻晃,落瓣簌簌飘,像是揉碎的云霞在飞。
无边艳色都被锁在了这里,再无半分路上所见的肃杀。
任谁也没有想到,影首有朝一日会在一人面前丢盔卸甲,会这般轻易地不战而逃。
摧信不自觉地抬手抚上心口处,那里跳动得极为剧烈,如同失了控般,令他感到有些惊异无措。
与殷无烬那热烈到近乎灼人的感情不同,因长久以来身处影门,他习惯了克制隐忍,再深厚的感情都会慢慢归于沉敛,更是能将情绪一贯保持平稳,在外人眼中便会显得冷漠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