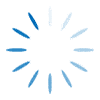“没什么……”
兰泽唇瓣微启,话音未落却又悄然合上,只隐约露出一点嫣红的舌尖,旋即被抿入唇间。
许是方才言语急促,又或是那几味奇药渐渐发散,令她的双颊泛起一层淡淡的胭脂色。
王群生凝视着她,不由想起兰泽自幼便是个多病的身子。
那些太医们偶尔会背着甄晓晴私下议论,说这位中宫嫡出的幼主先天不足,纵使用尽珍药将养,也难保长久康健,即便侥幸长大成人,亦必是孱弱之躯——在这金玉为堂、琼筵作室的宫闱之中,先帝这位最年幼的骨血,总比旁的皇子、皇女更显单薄。
犹记那年踏入宝观殿,他正遇见甄晓晴给兰泽喂药,彼时甄晓晴母仪天下已久,却尚未习得为母之道,眉间尽是不耐。那一身太后朝服极为厚重,周遭宫人垂手侍立着,她却偏不许旁人近前,只将十五六岁的兰泽死死箍在怀中。
兰泽挣脱不得,喉间溢出细弱呜咽,她含水的眼睛投向王群生,眼波里淌着哀恳,因着高热,身子亦不住打着寒战,瞧来可怜得紧。
王群生那时立在榻前,明知她在求救,想挣脱母亲桎梏,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甄晓晴撬开少年帝王齿关,将苦涩汤药徐徐灌入。
当汤药滚过喉管,兰泽眉尖蹙起深深的愁痕,待那苦涩的药汁终于见底,只留下一层淡淡的褐色水液,甄晓晴方不耐地起身。
接下来甄晓晴所言,王群生皆未入心。毕竟这位太后原是极好的权谋家、政治家、野心家,独独做不得慈母,亦非细致周到之人。待她领着宫人迤逦而去,王群生重新坐回榻边,见兰泽伏在床沿干呕不止。
这声响刺得人心头发紧。
默然良久,王群生取过宫人奉上的蜜饯递去。兰泽才尝一口,便吐入跟前的痰盂之中,一缕晶莹津液顺着她的舌尖垂落,黏腻湿润。
只听兰泽嗓音嘶哑道:“太甜腻了……我不爱吃这个……我身上太痛了,你可否替我求些止痛的汤药?”
这般形景,实在令人放心不下。
王群生却道:“陛下若再挑食,身子只怕愈发孱弱。皇后娘娘见了不悦,终究是殿下受苦。不如先用些肉羹……”他略微停顿,又添一句:“陛下如今的疼痛原是发热所致,待风寒消退,自然缓解。”
一语言毕,他便从床榻前利落起身,亲自从宫人托盘中接过热气蒸腾的肉羹。却见兰泽强撑病体,拽着锦衾往床里缩去,因方才呕吐之故,她眼周犹带红晕,虽未嚎啕大哭,但泪痕宛然。
王群生见此情景,险些维持不住面上得体,他柔声相问道:“这个也不合口?那陛下想用些什么?”
“此刻什么都不必了……”兰泽气息微弱,“你们且出去,这些时日莫来宝观殿,我不需你们喂食,不需你们看顾——”
王群生默然不语,但见兰泽撑在榻上的手臂微微发颤,不知是厌恶甄晓晴与他至此,还是病体已如风中残烛。泪珠倏然滚落,待她瘫软卧倒时,犹向宫人诉说着身上剧痛。
王群生终是放下手中青瓷碗,行至眼神涣散的兰泽跟前。缓缓探身入重重鲛绡帐幔,衣料摩挲声细细碎碎在耳畔流转。他忽地一顿,下意识抬手欲抚上那双泪眼,却觉臂上一沉。
原是兰泽攥住了他冰凉的衣袖。
“让我离开这里……去哪儿都好,”泪眼朦胧间,她迷迷蒙蒙地呢喃,“不管付出任何代价……再不愿受这束缚……”
兰泽掌心滚烫,几乎要灼透他袖上织金云纹。而王群生这般俯视的姿势,恰将她的脆弱、痛楚与迷茫尽收眼底,目光甚至可肆意游移至兰泽纤细的颈项。
因高热之故,她胸口急促起伏,终至眼皮半垂,只剩含糊呓语。王群生分明感知到这具病体已至强弩之末。
他多想将她拥入怀中安抚,可四下侍立的宫人,那些甄晓晴的眼线,迫他强抑冲动,只得如常藏起眼底眷恋,低声劝慰:“陛下……臣去寻止痛的药剂,您稍待片刻。”
兰泽原本紧攥他衣袖的指节微微松动。听得此言,似终于泄了心口那股气,将全部希冀寄托于他——那双白皙、纤细的手,顺着如水般衣袖滑落锦褥,发出沉沉一声轻响。
王群生至今仍能清晰地记起,兰泽的手从他衣袖滑落时,眼底对流露出对他的信任。
这份信任,在他心头盘踞了近十载。
“咳咳……”
一声压抑的轻咳将王群生从回忆中拽回,当他再次抬眸,但见身侧的兰泽以袖掩唇,双颊泛着与十年前那场高热相似的、不正常的红晕。
将近十年了,她从东宫至宝观殿,又从宝观殿迁至这邀月宫,身份几变,唯独这孱弱多病的身躯,一如往昔,甚至更糟。
“陛下?”他忍不住上前半步。
“没什么……”兰泽唇瓣微启,话音未落却又悄然合上,只对他摆了摆手,示意他退下。这平静无波之态,与记忆中拽着他衣袖哀求的少年帝王判若两人,只剩属于强撑的疏离。
王群生垂下眼,还是依礼退出邀月宫。
而这大殿之内,兰泽终于支撑不住,在他离去后颓然斜倚在座中,细细喘息。
这些时日她不仅要打理户部的各项开支,更要经略东南战事。连日的殚精竭虑,让她的身体比在东宫时还要孱弱,近来更添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症候。
如今春夏之交的清风,吹散京师连绵的阴雨,亦拂开江面层迭的战船帆影,不比舟山海雾弥漫的潮湿,此间更多是草木初生的清新气息,恍若天上人间的光景。
然这平静之下暗流汹涌——那舟山地处海疆中段,实为南北航线的咽喉要道。此地暗藏走私脉络,多有熟谙水道的老船工,兼以地形错综复杂,若敌寇在此获取补给、打探消息,实是易如反掌。
若其北上,则苏杭危殆。
若其南下,闽粤堪忧。
若其西进,宁绍平原这膏腴之地,便首当其冲。
且说四月间多起东南风,于帆船交战最是要紧。敌寇自东海来,恰是顺风扬帆,而官兵自大陆往去,却是逆风逆行,这在兵家看来,已是先失一着。
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,所有的压力最终都汇聚于她的案头。
“户部……”她只觉得思绪愈发混沌,总觉着诸事未曾料理妥当,处处尚有疏漏,可实在是心力交瘁,再难思量。
不知过了几时,外头传来几声清越的鸟鸣。她缓缓步出外殿,绫罗绸缎摩挲着娇嫩的肌肤,竟惹得浑身微微战栗。早有宫人陆续迎上前来,其中还有甄晓晴送来的那两个乐伎。她只觉头晕目眩,脚下虚软,好似踏在云絮之上。待萧亥桐上前搀扶,她也未曾推拒,由着他托住自己摇摇欲坠的身子。
远处晦暗的角落里,姬绥仍自匍匐在地。许是这些时日兰泽未曾来看顾他,此刻二人重逢,他竟是格外激动。待见兰泽近在咫尺,他顿时喜难自禁,猛地伸手攥住那纤细的脚踝,仿佛这是逃离无边苦海的唯一浮木,恨不得立时将她也拽入,同他一道沉沦至死。
但兰泽本就站立不稳,经他这般拉扯,只听环佩叮当,夹杂着宫人此起彼伏的惊呼。这回她终究没能稳住身形,踉跄着向下倒去——幸而底下还有姬绥这肉垫接着,才免了她皮肉之苦,不曾伤着分毫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